?
失落的西域文明
楊 鐮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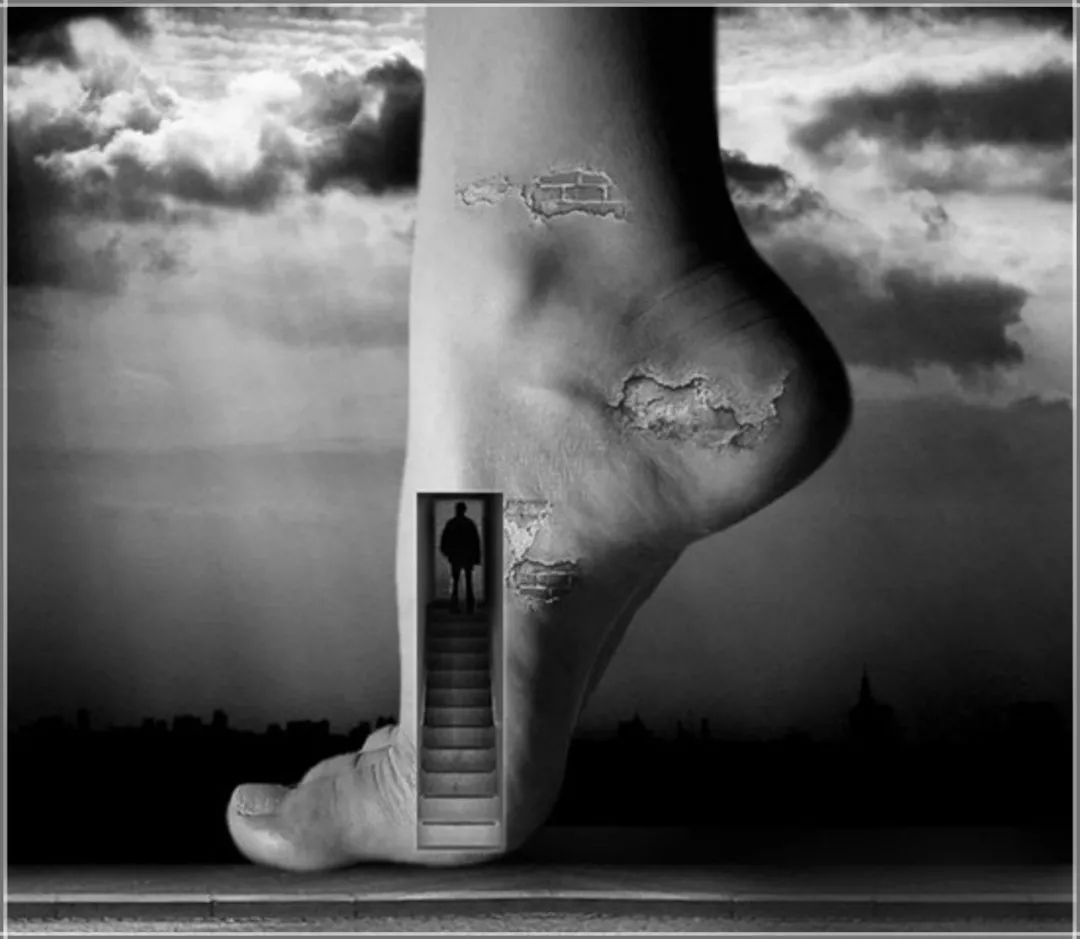
在網(wǎng)絡(luò)時代,信息發(fā)達、交通便利,絲綢之路是不是失去了它的意義了呢?又怎么理解在這個時代樓蘭是怎么能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的呢?
我們講的第一個問題,就是在中華文明史上樓蘭有怎樣的位置。在中國地圖上,南邊是海洋;東邊是海洋;北邊是西伯利亞的冰凍地帶,難以定居和生活,那么,在上古時期中華民族只有向西發(fā)展。凡是高度發(fā)達的文明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,就是要和其他文明進行交流,這是人類社會一個基本的推動力。中華民族到了秦漢的時候,已經(jīng)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之一,它要和別的文明交流。當(dāng)時人們還不能征服海洋,只有一條路,就是向西。雖然向西的路是那么坎坷漫長,越過武威,就是荒涼的河西走廊,除了嘉峪關(guān),走過河西走廊,又要沿著塔里木的一個一個綠洲前往中亞,在那里有著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和文明,除了自然條件惡劣,有很多的敵對勢力,有很多不穩(wěn)定的因素。即便是這樣,可以說從張騫通西域開始,向西發(fā)展,是中華文明與世界交流的惟一出路。有一個日本學(xué)者提出: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規(guī)律,那就是“南北對抗,東西交通”。實際上東西的交通,也就是中華文明面對世界的渠道。中原地區(qū)是華夏文明的發(fā)源地,在秦漢時期就很繁榮了。它的北邊是蒙古草原,匈奴、鮮卑等北方的民族必然的選擇就是南下,匈奴和漢朝的戰(zhàn)爭(南北對抗),促使了絲綢之路的興盛、東西交通的發(fā)展。

美國《國家地理》雜志到北京,曾經(jīng)對我作了一次專訪。采訪最后,荷蘭籍的導(dǎo)演提了一個問題,他說現(xiàn)在交通發(fā)達,通訊方便,進入了“因特網(wǎng)”時代。在這樣的狀況下,“絲綢之路”這個詞,會不會逐漸退出人們的視野。我說:絲綢之路現(xiàn)在實際上是一個象征,象征著人類文明的交流與進步,所以不但不會消失,反而會日益受到重視。
古人認為羅布泊的水潛入地下,又在青藏高原上冒了出來,向東流去便成了黃河,因此羅布泊是黃河真正的源頭。這表達出一種什么樣的觀念呢?
漢朝的中原地區(qū)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輝煌的文明,這個時候它需要和世界其他文明發(fā)生交流,舍西行別無他途。在西行的過程中,有一個地方是“瓶頸”,就是我們現(xiàn)在的羅布泊。當(dāng)年羅布泊浩渺無邊,號稱中亞地中海,是一個古海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上說它方圓幾百里,河水冬夏不增減。中國有一個傳統(tǒng)說法,就是“黃河重源說”,在《史記》和《漢書》成書的時候,中國的思想界和學(xué)術(shù)界認為黃河是從昆侖山流經(jīng)沙摸匯聚于羅布泊,再由羅布泊潛行地下幾百里,從星宿海、從青藏高原冒出地面,然后就流為中國河(黃河),這是見于正史的記載。這種說法當(dāng)然不對,因為第一,羅布泊早就干涸了,黃河源頭并沒有干涸;第二,星宿海比羅布泊地面高得多,水向低處流,不可能向高處流。但“黃河重源說”是我們中國最早的史地學(xué)家的認識,這種認識的實際含義,就是中華文明是從昆侖山發(fā)源的,和中原是通過黃河聯(lián)系起來的。但這種推斷不是科學(xué)的結(jié)論。

匈奴和漢朝爭奪樓蘭,誰具有了樓蘭,就等于有了“絲綢之路”的鑰匙。這么重要的一個地方,為什么突然之間就消失了呢?
羅布泊在漢朝是非常大的水域,東西的行人,必須經(jīng)過羅布泊,從那里得到水,補充給養(yǎng),尋找新的向?qū)В匦抡{(diào)整駝隊。在羅布泊的岸邊有一個古老的國家叫樓蘭,因為中華文明需要和世界其他文明進行交流,這樣才把樓蘭這么一個小小的國家引人了我們中國的歷史。在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里都有關(guān)于樓蘭的專門的章節(jié),內(nèi)容非常豐富。大家知道很多關(guān)于樓蘭的故事。比如,匈奴和漢朝爭奪樓蘭,誰具有了樓蘭,就等于有了“絲綢之路”的鑰匙。班超出西域時,為了使樓蘭傾向漢朝,就在一個晚上用突然襲擊的方式,帶領(lǐng)部下把匈奴的使者殺了,這樣樓蘭只有傾向漢朝了,這是正史上記載的故事。另外一個故事,就是傅介子刺殺樓蘭王,這個在正史上也有記載,后來唐人根據(jù)這個寫出“黃沙百戰(zhàn)穿金甲,不破樓蘭終不還”的詩句。

有一個德國學(xué)者寫了一本書,名叫《樓蘭》,他說樓蘭這個國家是“緊張的國際關(guān)系的紀念碑”。漢朝的時候,匈奴和漢爭奪西行通道的控制權(quán),誰能得到西行通道的控制權(quán),誰就有進一步的發(fā)展,否則便受到遏制。所以樓蘭也被牽入了征戰(zhàn)。這就是歷史上的樓蘭。樓蘭第一次在《漢書》中出現(xiàn)是描寫在漢文帝時期,匈奴給漢朝寫了一份通牒,列出西北已經(jīng)歸屬匈奴的國家,里面就有樓蘭,這是樓蘭第一次出現(xiàn)在中國的史冊上。然后張騫通西域,張騫的駝隊通過了陽關(guān),經(jīng)過了非常荒涼寂寞的河西走廊,突然發(fā)現(xiàn)了羅布泊岸邊出現(xiàn)了村落,村落里的百姓不同于漢朝的民眾,說的話也聽不懂,樓蘭王國與他的臣民首次接待了漢朝的使節(jié)。樓蘭民族怎么到達羅布泊的,從哪來的,到哪去了,現(xiàn)在都是一個謎。我們已經(jīng)知道它的歷史至少有3800年,建國至少700年才滅亡,可以肯定樓蘭人的語言是印歐語系的語言,跟河西走廊以東完全不一樣。他們的文明也有自己的獨特內(nèi)涵。就這樣,樓蘭進入了中華民族的歷史,在中西文明進行交流的過程中發(fā)揮了巨大的作用。

樓蘭一直處在漢朝和匈奴兩強中間。一個只有14000人的小國,在兩個強大的政權(quán)中間無法自處,最后要求漢朝派部隊保護它,漢朝于是派了一支部隊在現(xiàn)在新疆的米蘭(史書上叫做伊循城)駐扎屯田。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西部屯墾戍邊。經(jīng)過李廣利、衛(wèi)青、霍去病幾代將軍的戰(zhàn)爭,漢朝終于擊潰了匈奴,中原政權(quán)就在樓蘭設(shè)立了西域長史,管理這個地區(qū)。但是到了公元5世紀的時候,這個國家突然沒有了。我在一本書中這么形容樓蘭的消失:就像一個內(nèi)陸河流經(jīng)沙漠,忽然一個晚上就徹底不見了——完全潛入地下。中國史冊的記載證明,在5世紀的時候樓蘭被一個叫丁零的部落所滅,樓蘭國王帶著4000人放棄了首都逃亡到且末。這是“二十四史”中有關(guān)樓蘭的最后一條記載,從此以后這個國家、民族就從中國歷史中消失了。唐初玄奘從印度取經(jīng)回來,路過羅布泊,他說這里“城廓巋然,人煙斷絕”,已經(jīng)非常荒涼。

樓蘭的再次發(fā)現(xiàn)是在100年以前。這次對樓蘭的發(fā)現(xiàn),是考古學(xué)、民族學(xué)等等新文化進入中國的一個起點。時隔兩千多年后,樓蘭又一次牽動了中國。
20世紀的新疆史,是重新發(fā)現(xiàn)西部的歷史。很多探險家到西部去,在新疆發(fā)現(xiàn)了流沙掩埋的發(fā)達的文明。有一個探險家曾經(jīng)在庫木圖拉附近的一座塔中找到了一摞樺樹皮,研究者確認這是3世紀手寫的書,是用印度古文字寫的。這就是世界著名的“鮑爾古本”。在新疆發(fā)現(xiàn)了古城,發(fā)現(xiàn)了高度發(fā)達的古代文明的消息,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傳遍了歐洲,所以當(dāng)時到新疆來探險就成了地理大發(fā)現(xiàn)的余波。20世紀到新疆的探險家,最重要的是兩個人,即瑞典人斯文·赫定和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。主要通過這兩個人的工作,突然使寂寞的新疆進入了人們的視野。人們突然發(fā)現(xiàn),在流沙之下,竟然掩埋著高度發(fā)達的文化,有文字,有古老的佛教文化,有建筑遺址,它證明了絲綢之路確實曾經(jīng)繁榮過。自從探險家進入了新疆至今,絲綢之路熱一直沒有停止過。
斯文·赫定和斯坦因這兩個探險家有兩個共同的地方,都是終身未娶而且都是著作等身,出了很多很多書。他們的書成了關(guān)于新疆探險發(fā)現(xiàn)的經(jīng)典。在中國西部的發(fā)現(xiàn),使這兩個人成了爵士。斯文·赫定是瑞典最后一個被國王封為貴族的人,斯坦因則由英國女王封為爵士,他們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榮譽,但是也受到了很多
掃一掃在手機打開當(dāng)前頁